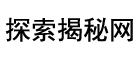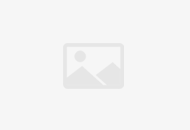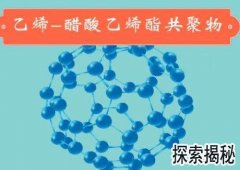毛邦初事件,他的名字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这个人就是杨靖宇将军。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在他牺牲后,日本人人为了羞辱他,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墙上,以此来嘲讽中国人。那么,杨靖宇将军究竟有多厉害呢?他的头颅到底值多少钱?为什么日本本人要如此残忍的对待他的头颅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抗日名将的传奇人生。杨靖宇出生于1905年,辽宁省大连市人。
一:毛邦初旧宅
95公里。宁波殴华亭酒店位于宁波市象城县步峰路,奉化毛邦初旧宅位于宁波市奉化区武岭西路,根据百度地图显示可知,两地相距95公里,驾车前玩需花费1个小时20分钟。二:毛邦初和蒋介石的关系
1944年2月25日,第2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74军军长王耀武,因功擢升新组建的第24集团军总司令,这就意味着第74军军长的宝座出缺。正在贵州遵义地区(师管区)训练新兵的副军长李天霞闻讯,立即从后方赶往前线军部所在地湖南邵阳,在他看来,接掌这个王牌军军长之职的人选,非他莫属。
李天霞,黄埔三期毕业生,民国时期的江苏宝山人氏,放到今天就是妥妥的上海市区户口。李天霞自幼家境殷实,年轻轻轻就喜欢上了按摩足疗大保健等项目,最爱去的就是虹口区的日本按摩院,属于黄埔军校中最早一批“奋起抗日”的学员。黄埔建校时的1924年,18岁的李天霞已经在上海的北四川路、海宁路一带小有名气,无非就是挥金如土,敢结三教九流。
在体育老师的引导下,李天霞逐渐有了进步思想,1925年4月与毛邦初、方先觉等几十名青年共同前往广州,就读黄埔军校第三期。北伐战后,李天霞已升任第3师少校营长,驻军上海曹家渡,但之后仕途一直不顺,干了将近四年的中校团副也没有转正,直到担任保定编练处中校团副期间,终于撞见了“贵人”王耀武。时王耀武奉命执掌新组建的补充第一旅,而该旅官兵基本出自保定陆军编练处(处长钱大钧)。
为了拉拢李天霞从而搭上钱大均这条线,王耀武保举李天霞出任补一旅第三团上校团长,从此王李二人搭起了班子。1936年补一旅扩编为第51师,李天霞水涨船高成为该师少将副师长,淞沪会战爆发后第51师和58师合组第74军,李天霞以51师少将副师长兼153旅旅长,手下两个团长分别是张灵甫和邱维达,因此可以说,李天霞确实是王耀武军事集团早期的二号人物。
实事求是地说,李天霞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淞沪会战为掩护大军西撤,曾率153旅在京沪铁路大桥与日寇血战三天三夜。南京保卫战,登上城墙力战不休,最后渡江脱险。武汉会战期间外调第40师师长,在庐山战斗中也与敌重大杀伤。1939年6月,王耀武晋升第74军军长,而李天霞顺理成章擢升第51师师长,这一期间,如果仅靠吹牛拍马而不是战功,李天霞不可能扶正王牌师师长。
1941年春,王耀武率军参加上高会战,李天霞第51师在战场南路大破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为上高大捷立下汗马功劳,战后51师获“第一号陆海空军武功状”,这个荣誉是很有点含金量的,余程万57师才是“第二号武功状”。1943年晋升第74军中将副军长兼贵州镇远师管区司令,负责为第74军训练和补充新兵,正是在这一期间,第74军发生剧烈的人事变动。
可惜王耀武还是有些偏向张灵甫的,一方面是李天霞与其资历相当不好控制,另一方面是王耀武当时已经“通天”,李天霞失去了利用价值,而张灵甫当时只是个师长还不够级别接班。于是王耀武来了一个“移花接木”,调集团军所属第100军军长施中诚回任74军军长,然后再保举李天霞继任,这样操作的结果就是,李天霞虽然升职晋级,却被踢出了第74军系统,从此与军长宝座无缘。
李天霞心中有苦说不出,毕竟已经成为了中将军长,也算是王耀武集团的嫡系部队。抗日战争胜利后,第100军改制为整编第83师,李天霞又成为了中将整编师长,先厚在李默庵、汤恩伯的指挥之下,于是才有了孟良崮战役中的“千里救援李天霞”。
不过抗战以后,李天霞作战不那么卖力气了,贪财好色的本性开始显露,不复抗战时期的悍勇,所以无论怎么开脱,战役初期李天霞100%有看张灵甫笑话的念头,只是他有两个想不到:第一是张灵甫能被全歼,第二是老蒋后面真急眼了。
1947年5月17日,整编第74师全军覆灭,老蒋追魂电到达:“汤恩伯撤职查办,李天霞就地枪决”!但是在顾祝同、汤恩伯的包庇下,以及李天霞流水一般的金条花出去,到达南京即被保释。随着汤恩伯、黄百韬在军事检讨会议上翻盘成功,6月间李天霞还获得三等云麾勋章(黄百韬才混了个四等),不久复出担任绥靖区副司令,以及第37军军长等职务,全身而退。
1949年9月,李天霞转任福建平潭防卫指挥官兼重建的第73军军长,仍然隶属于汤恩伯指挥,结果在三野十兵团的打击下土崩瓦解,随即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一年之后在黄埔系几位大佬的求情之下获释,从此离开军界,1967年离世。
三:毛帮初的后代
本文
“非战之罪,何罪之有!”——探秘抗战空军真实战力之一(预警、指挥篇)
从2016年起,台湾纪录片《冲天》在大陆网络上广泛流传开始,
很多读者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不是讲空军飞机装备,因为在笔者的心目中,预警指挥系统才是在抗战中决定空战胜负的最大因素。
中国的防空预警情报网始建于1934年秋的南京防空演习,由于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地面没有一部雷达,为了方便对敌机进行监控预警,国民政府建立了大量的防空监视队(哨)。
根据时任国民政府防空总监黄镇球所著《首次防空节来谈我国防空之创造作战及演进》(1940年)记载:“到抗战全面爆发时,全国共计成立有205个省防空监视队、1345个防空监视哨、104个独立防空监视哨。”这些监视哨人员携带通信工具配置在各大城市周围100—250公里的地境,当日机飞临时,情报人员就将飞机数量、飞行方向乃至机种逐次传递,以使预警区做好防空准备。然而,由于天气、通信故障、人为判断失误等种种原因,防空预警不及时和误报带来的后果,让中国空军吃尽了苦头。
1937年11月22日,日军木更津航空队11架96陆攻空袭我周家口机场,此时机场中正好有我第四大队15架战机准备在此转场飞往南京参战。由于战前建设不利,机场连防空警报系统都没有安装,到日机快飞临机场时,我方均无日机来袭的警示。直到午饭后,机场站长张明舜才向高志航紧急报告有空袭警报。高志航当即命令全部战机火速强行起飞,然而他的伊-16-6战机却因发动机始终未能启动,在日机的轰炸下不幸殉国。高志航的牺牲对中国空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如果当日防空预警来的及时准确,断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时任第三大队飞行员的江秀英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更是以亲身经历,多次提及防空预警的重要性:“1940年1月8日下午3时许,敌侦察机一架来犯,敌机到永福县上空时机场指挥部始得到情报,刘副司令命我起飞迎击,当我起飞升空到1500公尺时,敌侦察机正由我机上空通过,其高度约3500公尺,敌机身是银灰色的,在太阳光反射下,看得一清二楚,敌高我低,有2000公尺高度差,我无法攻击它,只好眼巴巴的望着它从机场上空通过,停在机场上一大队飞机,可能已被它拍照。
我降落后与巴布什针大队长(注:苏联志愿航空队)一同去问刘副司令,为什么敌机到了头顶才知道?刘说现有的防空通讯,全是利用广西省原有的乡村有线电话传送情报,一个县一个县传送,有时电话还叫不通,那就无法及时了。巴大队长再三强调,防空作战的胜负,主要取决于情报是否来的及时,为有利于今后作战,希望加强情报电讯工作…刘说今后尽力争取情报快达。话虽如此,但情报并没有什么改进。”
“1月16日晨7时许,我们刚进入机场待机室,即听到隆隆的机声,根据以往的经验,无疑这是敌轰炸机群的声音,我们冲出待机室,即见敌94式轰炸机14架如一群大雁,整齐的人字队形,从机场西南侧空间进入…那天各机正在加油,尚未推入机场,敌机利用拂晓偷袭,事前没有得到情报,无法起飞迎击,眼巴巴的看着几十个炸弹落在停机地带,大家都以为这几十架飞机必然凶多吉少,航空站站长梁启昌见到此情,深感责任重大,未等查明损失,就举枪自杀。幸得他的勤务兵手快,在他身后见他拔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时即迅速托起他拿枪的手,因此子弹只擦破头皮,救了他这条命。
敌机离去约20分钟,机械长来报告,飞机全完好,无一受创,弹着点都离飞机有四五十尺远,机械员也全部平安无事,实属不幸中之万幸。当时在场的几十张像死人一样惊呆了的面孔,顿时变成惊奇的微笑,刘副司令铁青的脸上也泛起一身松的笑容,一向乐哈哈的巴大队长,当他看到敌弹全在停机地带投落时,脸部像停了呼吸一样没有一点血色,得知全部飞机安全无损时,才恢复常态,他张开双臂仰天大笑…大家讨论为什么没有情报,据赶来机场了解情况的陈参谋说,是由于平乐至荔浦间电话线断了,所以情报传不到。巴大队长说要用无线电话,才能适应战时需要,刘副司令也口头答应尽量想办法,但后来的事实再次证明他仍是临时应付而已…”
“1月23日9时许,得到敌机来袭的情报,但机种、数量、高度全不知道。机场飞机全部依次升空警戒,当我们上升到3500公尺高度时,在我机群上空出现了敌机,其高度在4200公尺左右,是新出现的97式驱逐机,速度较我方略快,灵敏性也优于我方,共9架。论机数是我多敌少,但敌快我慢,敌高我低,我们无法攻击它…前后经过仅五六分钟,即结束了战斗。我方损失两机,原因仍是情报迟缓,如能早起飞十分钟,我们能与敌等高的话不至有此损失,如能居于高位,我机多于敌方,胜利无疑属于我方…”
“1月26日上午10时许,又得敌机来袭的情报。大家吸取上几次教训,飞行员到机场后都各自坐在机旁草地上待命,不到5分钟全部飞机都已升空,当机群上升到3000公尺时,敌机已在我机群上空出现。又是情报来迟了。那天是晴天,敌机以两机对我领队机攻击,我领队机由于阳光耀眼,敌机来攻时竟因回避不及被敌击中,巴布什针中校不幸中弹,当即壮烈牺牲。我们在后的机群,由于高度低,机速慢,无法支援,大队长的牺牲仍是情报来迟的缘故。”
空战中,交战双方谁能掌握空优高度,谁就能最大限度的掌握制空权,这也是决定空战胜负的关键。日机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优于我军,经常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而我方则被迫进入防御态势,再加上日军欺骗战术或天气限制等因素,影响我军情报的判断,经常是警报不断,飞行员疲于奔命,却不见敌机来袭,或者警报响起,敌机已临空,造成来不及起飞,低空遇袭的情况。即便防空预警情况及时准确,但指挥官的判断、紧急起飞令下达的时间,才是空战胜负的另一个关键。
让我们先来看一段刘毅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著《空军史话》中对武汉4.29空战的描述:“突然姜参谋大叫:'机三批沿江飞来,第一批快到黄岗了!'我不用看地图,也已晓得这个距离,早已进入了紧急警报圈了,我急匆匆地问他:'为什么还不起飞呀?'我问的是姜参谋,实际上也是提醒兼参谋长的邢铲非,等我进房里,他长长叹口气说:'总指挥部不准起飞呀,我问过啦,他认为时间太早。'我毫不考虑的顶碰他说:'这是什么道理?敌机如果飞在七千尺高空,一到黄岗就可看到了我们的飞机场,黄岗到王家墩只有二十公里啊!'”
“突然情报电话又响了,邢铲非接电话,他耳听,眼睛焦急的望着我们,嘴里小声复颂:'敌机三批,都是驱逐机,第一批已过黄岗!'我急得跳起来,凭我在大教场的经验,再不起飞,我们在王家墩的一百多架战斗机,再也来不及全数离地了,更不用谈战斗,我几乎用出要爆炸的声音,但仍是哀求的口吻:'总站长,快接黑旗命令紧急起飞吧,拉红旗子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起飞,已经不够跑道了,战斗一定要吃亏,再迟疑我们全部空军力量都要被敌人打地靶了。'”
“总站长也很难过,姜参谋、张参谋都因阶级低,不敢讲话,但总站长终于又用犯上的冒险精神打了请求起飞电话,结果被上边一口拒绝了的理由是:我们如果早起飞,油是不够,太危险…这真是,哎!”
“我立刻急出了眼泪,我看看窗外机场上四周的一百五十架飞机,和那些可爱可敬的年轻飞行员,这是我们国家仅有的起死回生的力量啊,如果今天一下子被日机打光,武汉也将立即不保,国家啊,想拼死杀敌的空军哥儿们必将抱恨终天,我们若干淞沪牺牲的陆军与首都沦陷时死亡的军民也将魂兮饮恨了。”
“我陡然又想到了,总站长是军人,我还是客串的半个军人,军人讲服从,客串就不必这一套,好吧。于是不再迟疑,头也不回的跑到门前,跑到警报旗杆下边,我飞快的取下绿旗和红旗,急急拉起紧急起飞的黑旗。”
“黑旗升空,整个机场立即爆发了战斗的活力,所有人都在动,飞行员跳上了飞机,地勤人员开始摇车,对面的四大队干得最快,毛瀛初、董明德等首先开车起飞了,其余所有飞机也都先后开了车向起飞位置滑行,全场叫起了怕人的马达吼声。姜参谋用满脸笑容看着我,但他眼上挂着一串激动的泪珠,总站长皱眉不语心神不安的望着我,小老弟张参谋在门口搓着手看着我,都像似在心里说——你立了大功,也犯了大罪。”
“我平静的望望天空,已有五十多架飞机,爬到了一千尺,还有五十多架刚刚离地,也有的仍在跑道上加油门起飞,还有二十多架仍在场边向跑道滑行,两架可塞也在等警报黑旗挂起后,忙着落地又起飞,一切都显得很紧张,匆忙,也有些混乱。自从空军打仗以来,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紧急起飞,飞机场上还有十多架老毛病的飞机,无法开车,飞行员便跳下飞机,往总站跑。”
“我挂了旗,冒了生命危险,尽了国民之责,进到总站里准备接受宪兵的拘禁,刚刚进了房,总指挥部的电话来了,我以为这一定是要抓我的电话了,心里却不恐慌,也不羞愧,因为我已听到了日本九六飞机向机场俯冲的声音,同时也隔着敞开的窗子,看见两架九六正冲向刚刚起飞的可塞教练机,我心里为这两架即将牺牲的羔羊痛苦。”
“电话是总指挥来的,我隔了几尺远还听到铿铿骂人声,我只能听清楚邢总站长说:'是…是…不敢…是,是刘兴亚挂的黑旗(我的本名),'事后邢总站长告诉我,总指挥第一句就要枪毙我,等我说是你挂的黑旗,他嘟噜了一句,我未听清楚,当即见到两架九六冲下来,把两架可塞打得起火掉下来,他才不骂了;也因此我未受到军法处刑。”
“第一批临空的三十六架敌人的九六战斗机,已经和我们升空飞到一千尺高度的伊—16打上了,我其余已起飞的飞机仍在爬高,敌人第二批飞机也未临空,如果它们再早到一分钟,我们虽不至于全军覆没,但损失必定够惨了。就是这样,我们已经够狼狈了,先起飞的四大队飞机,都是先挨打后反抗,幸而无人被打下去,起飞较晚的二十四队,刚离地就挨打…”
刘毅夫时任空军励志社(空军俱乐部)人员、
曾参加过武汉空战的吴鼎臣在《忆抗日悲壮岁月》中这样记载:“当我们飞到四千米高度时,就与比我们飞得高的日本战斗机相遇,显然处于劣势。为什么我们会常常处于劣势呢?因为机场上的指挥很混乱,当时机场上除了我们的战斗机以外,还停有轰炸机和不能作战的飞机,一有警报,这些飞机先要飞到别处去躲避,以免留在机场遭到敌机的轰炸。我们战斗机是编队起飞的,起飞后再尽量升高。由于我们起飞晚,往往尚未升到足够的高度,就和敌机碰上了,同时指挥部规定,我们的飞机不能够离开武汉三镇的上空,敌机飞得高,很容易就发现我们,而我们则不容易找到他们。”
抗战期间,空军指挥系统因为错误的观念,迟迟不下达起飞命令,造成我空军部队次次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样的情形甚至延续到抗战后期。
1943年6月6日,大批日机来袭梁山机场。当时防空监视哨向驻梁山场站第1路司令杨鸿霄报告发现不明标志的12架飞机(敌机实为22架,有10架未被发现)正向梁山飞来。杨鸿霄误以为这是从前方作战归来的中国飞机,当时机场上各战斗部队的分队长都要求起飞,但他优柔寡断,仅令飞行员机前待命,而继续与重庆商议,等到万县情报到达:“F(敌机)8,3点—9点,正向梁山飞行!”这时杨鸿霄才下令紧急起飞,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场战斗中,周志开虽然单机强行起飞,击落3架日机,获得空军首枚青天白日勋章,但空军王牌四大队的飞机在机场上被日机打了地靶,大队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事后,杨鸿霄被撤去司令职务。
为什么指挥系统拖了空军的大腿呢?这主要归咎于空军制度体系建设上的缺陷。空军的作战指挥体系,主要由笕桥航空班(中央航校一期)组成,这批83人是由陆军黄埔第五、六期和军官团学员带阶转入,在笕桥接受短期的训练。但由于当时环境和设备所限,他们训练不足,仅具有基础飞行的经验,当然更谈不上空军的战技、战术思想。但由于他们阶级较高,自然就分别担任地面高阶指挥、高司参谋之职。
中央航校二期及以后的学员,则是由黄埔八期及以后的军官和民间大学招生而来,接收完整的飞行训练,毕业后以准尉任职。这就造成了高阶无实战经验的领导指挥低阶作战的怪现象。蒋介石让陆军出生的周至柔取代广东航校出生的毛邦初担任空军的实际负责人,这种从上至下的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造成抗战仅过半年时间,我空军上百名飞行员牺牲的惨痛代价。张光明将军曾经回忆说,中日开战年余,每次空战我方均居高度劣势,次次挨打,此状况延续到1939年“五三”重庆空战时,由毛邦初将军指挥,才得以改善,这也是第一次中方取得空优高度的作战。
而空军制度体系建设上的这种缺陷,更是由于空军成军时间短(1936年全国空军才得以统一,而37年抗战就全面爆发),我空军重要军职无法循序渐进的历练升职所造成的。
那么前文提到的空军指挥系统错误的观念又是什么呢?时任第四大队二十二队中尉飞行员的张光明曾亲眼目睹,在武汉二一八空战中,四大队大队长、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李桂丹,由于起飞时间过晚,其座机在爬升的过程中就被日机从高空俯冲,仅一轮射击,便击落殉职。张光明晚年在《圣地亚哥航太博物馆参观记》一文中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空战中战斗机展现猛烈的攻击时,本身没有防卫能力,端赖编队僚机的支援或高空域在空机的掩护。因此高度的获得,就争取到攻击的主动。中日空战前期,当时防空情报监哨不足与疏漏,敌机在中国之土地上到处飞,由于通讯情报不灵,已处被动状态,加上地面指挥官的素质,只要飞机不被打在地面的心态,起飞了再说,调度是否适当,死亡多少人,均与他无关。”
“1938年2月18日汉口空战,总领队机组4机,刚起飞至一千尺就遭攻击,4机中3机瞬间被击落。再好的飞机、再能战的飞行员,起飞中被攻击,也是没办法的;但指挥官却没责任。形成了只要飞机上了天,生死存亡全由飞行员自理的怪现象!”
“直到1941年天水机场被打地靶,16架伊—153战机被毁于地面,五大队番号被撤,挂上'耻'字,成了无名大队,天水站长被撤职送军法。此实非战之罪,亦让五大队全体飞行员蒙羞,乃历史的伤痛,指挥高层不了解空军之特性与机种的性能,以指挥陆军地面部队,以数量多寡定胜负的观念,又何能致胜?”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都了解了预警和指挥系统的重要性。抗战期间,我空军健儿与日军航空兵在空中短兵交接之前,其实在地面上就已经先输了半个子,这也是为什么从武汉会战开始,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我空军战机对日机的交换比会如此难看的原因之一。
就如张光明将军所言:“此实非战之罪,何罪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