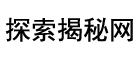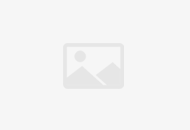【编者按】
2024年7月29日,在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中国游戏开发者大会(CGDC)“游戏音乐主题论坛”上,《沪游叙事·上海网络游戏产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沪游叙事》)进行发布。
《沪游叙事》由澎湃新闻旗下智库澎湃研究所主编,以详实的案例、一线的调研论证了“上海何以为重镇”,从产业纵深、发展切面、案例特写以及发展建议等角度出发,描绘上海网络游戏产业激荡二十年的发展图景。澎湃研究所将陆续刊发《沪游叙事》报告中的文章。本文为“发展切面”章节中的第一篇《游戏文化:电子游戏能算是艺术吗?未来的艺术与艺术的未来》。
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电子游戏的飞速发展是人类文化历史上的巨大奇迹,不仅赢得年轻一代的狂热拥护,还正从电影电视等强大的主流文化产品中抢夺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根据数据调研机构Newzoo发布的报告,2023年全球游戏产业市场总值达到1877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6%。相比之下,2019年全球电影票房为339亿美元,就市场规模而言,已经远远被游戏业抛在后面。
2003年11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将电子竞技列为第99个正式体育竞赛项目。每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数字产业展会,也是数十万游戏玩家们的狂欢盛会。
2024年7月26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观众在体验《崩坏:星穹铁道》游戏场景。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对于电子游戏这种“另类”文化形态咄咄逼人的崛起,国内外的学术界也正在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已经有人在欢呼“第九艺术”的诞生。电子游戏能算是艺术吗?它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艺术?它与已有的艺术在哪些方面具有可比性,有哪些独特性和潜在的可能性,对传统的艺术形态和观念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这些都是非常值得人文科学工作者严肃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
电子游戏的艺术性:情感的强化与媒介的力量
电子游戏能算是艺术吗?英国艺术批评家乔纳森·琼斯认为:“电子游戏创造的世界更像是游乐场,体验是由玩家和程序之间的互动创造的。玩家无法将个人的生活愿景加于游戏,而游戏的创造者也放弃了这一责任。没有人‘拥有’游戏,因此没有艺术家,因此也没有艺术作品。这是游戏与艺术的本质区别。”[1]像小岛秀夫、约翰·卡马克等游戏业内的著名人士,都对游戏的艺术性有过很多否定性的言论。游戏最早是不标作者的,但是这种情况在后来其实有很大变化,今天的知名游戏都会强调是谁开发的。
琼斯从传统的作者性的角度否定了游戏的艺术性,但是他忽略了现代艺术、文艺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现代艺术的重心恰恰是越来越朝读者、观众或是玩家的方向倾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琼斯对游戏艺术性的否定,恰恰可以成为对游戏艺术性的支持,即现代艺术要挣脱作者的束缚,把选择权越来越交给读者、观众和玩家。
例如游戏《仙剑奇侠传》画面以四十五度斜向绘制,插配活灵活现的角色动画,描绘出士农工商诸如耕种、钓鱼、养鸡、打铁、洗衣等民风民俗。更时有松柏仙鹤、渔樵流水,配以丝竹之乐,烘托出古色古香的中国传统风味。与传统的武侠小说不同,仙剑通过电子游戏独有的特点,把自身的艺术性放大。在通过观看、搜索、打斗、解谜、对话等一系列的操作后,“仙剑迷”们把自我投射在游戏的虚幻角色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与传统文学艺术相比,电子游戏更注重玩家的体验,这种体验不仅是视觉和听觉的,也不仅仅是语言文字激发的想象,而是由玩家通过身体性的操作,将多种感官与大脑的活动进行整合。游戏研究者格兰特·塔维诺(Grant Tavinor)认为:“电子游戏具有推动艺术发展的巨大潜能,就在于它能将观众拉进虚构的世界中,把虚构的情感与动作结合起来。电子游戏是交互性的小说,让玩家在游戏世界里既成为认知的主体,又成为行动的主体,他们因此就能够对那个虚构的世界发生影响,从而引导他们自身的行动。这也意味着电子游戏中的情感对于艺术哲学来说有着更为重大的潜在意义。”[2]
从某种意义上,电子游戏具有不同程度的“角色扮演”意味,过程有点像表演性的戏剧,但玩家不仅是传统的观众,也是舞台上的演员,而整个游戏空间的广阔性和自由度又大大超过了传统的舞台,让玩家能在其中尽情发挥和自我陶醉,体验创造、表演和观赏的三重快感。
电子游戏对情感的制造和强化,正是其媒介性的体现。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是人的延伸”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大多数技术都产生一种放大效应,该效应在感知的分离中是十分明晰的。广播是声象的延伸,高保真的照相是视象的延伸。而电视首先是触觉的延伸,它涉及所有感官的最大限度的相互作用。”[3]麦克卢汉如果活到今天,他会看到电子游戏为感官的强化增添了全新的维度:身体。
早期的电子游戏玩家是用简单的游戏杆或者鼠标键盘进行操控,身体的动作及其与游戏世界的互动非常有限。在今天,游戏硬件飞速发展,对玩家身体的开发和利用也日新月异。从带有各种力量反馈的新型游戏手柄,到Kinect、WII和Switch的体感控制器,再到六度空间的人体定位、手势识别和眼球追踪,现实玩家的举手抬足,甚至每个眼神都能被游戏识别感应,也让玩家与自己投射的对象产生更大的认同、更深的沉浸与更强烈的情感反应。
麦克卢汉肯定技术和媒介的力量,但他也对其滥用保持警惕:“为了放大或增加人体官能的力量,我们放任自己,我们自我异化,这是邪恶的花朵或赘生物。”情感是人类的纽带,也是所有艺术的基础。了解情感在电子游戏中的构成方式,因势利导,去粗取精,用而有度,对于推动游戏产业和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我又不是我”:电子游戏带来的视角解放
新的艺术媒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感,也带来了新的视角。在文学艺术中,叙事视角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作品的存在方式。同样,视角在电子游戏中也是一个极为核心的问题。玩家的视角既是客观视角,又包含了主观的成分,在传统的文学写作中很难看到。那个“我”既是我,又不是我,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一方面,我站在我以外的地方看见“我”自己,仿佛灵魂出窍;另一方面,我对这个“我”拥有全部的操纵权;这个屏幕上的“我”同我极不相像。游戏中这种奇特的视角及其效应充分说明了主体性的脆弱和自相矛盾。
不光有人的视角,还有动物的视角。例如,在冒险游戏《坏虫》中,玩家所扮演的是蟑螂,这简直就是卡夫卡《变形记》的翻版,以更为直观和体验化的形态呈现,与从动物视角切入人类社会的先锋文学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玩完这个游戏,你会对危机四伏的蟑螂以及与此不无关联的人类自己的生活有全新理解。后现代是一个“视界融合”的时代,我们被各种各样的眼睛看,我们也用各种各样的眼睛去看,而电子游戏就是我们在新时代观看世界的新的眼睛。
游戏研究者A.L.贝克认为:“我们已经看到,玩家在玩游戏时可以有效地了解他们的玩家角色的各个方面(有时通过受调节的交互性再现),而这在传统的演员与角色的关系中不会发生……在其他任何媒体中,都不可能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将世界作为微风、神灵或电子游戏可能使用的任何其他无数潜在化身 (avatar)对世界采取行动的感觉。”[4]例如在陈星汉的游戏《花》中,玩家可以扮演一股风,吹过城市,吹过原野,吹过草木花卉,为它们吹进生机。
在电子游戏的发展过程中,视角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电脑3D技术的进步,使得多重视角成为电子游戏在叙事过程中天然的巨大优势。很多冒险射击游戏都允许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主人公的活动,像FIFA和NBA系列的体育游戏也可以在比赛时任意地切换摄影机的角度。可以俯视,也可以四十五度角斜视,还可以用镜头追踪或者镜头漫游的方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杰姆逊认为,视角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形式的问题,其本质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为什么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会出现透视法呢?这是和笛卡尔的‘意识即中心’的观点相联系,和西方新兴的关于科学的观念相联系的,此外还有自然的统一化,以及商业的兴起等等原因。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到透视的出现是和经济、科学的发展,以及空间和人对自己身体的认识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5] 到了现代,西方人不再相信透视是认识现实的惟一方法。现代主义绘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摧毁透视、摧毁画框带来的整体性,要冲出的不仅是一种风格体裁,而且是一整套意识形态。
从作者到读者:媒介的融合与艺术的共创
什么是艺术?几千年来人们对此争论不休,有一个电子虚拟社交游戏对此提供了他们的答案:“第二人生”。这是一个基于网络的虚拟世界,其玩家在游戏里叫做“居民”,通过移动的虚拟化身互相交流,参加个人或集体活动,制造可以出售的虚拟物品,甚至可以买卖虚拟的地产,从中获得真实的金钱。对“第二人生”的居民来说,艺术就是通过创造可能的人物与可能的世界,让人们突破真实世界的束缚,进行想象性的自我超越与自我实现。
这又何尝不是艺术的目的呢?但在传统艺术中,可能的世界是有限的,自我超越也是有限。更具体地说,就是受到各种艺术媒体的限制。传统的文学作品一旦制作完成,其物理形态便固定了下来,这是一个一次性的创造过程,而读者的阅读过程也不得不呈现出线性的特征。尽管如此,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读者一直是最具推动性的因素,文学面向读者的运作过程变得越来越明显,文学批评中也出现了读者反映批评、接受美学、阐释学等理论,文学的重心开始从作者向读者转移。
有意思的是,这些以读者为中心的理论的提出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游戏,把游戏视为文本的开放性的原型。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阅读总是在选择中突出对象:或者是多样化的选择,这意味着包纳游戏的多种可能性,或者它自己开放于各种变化的反动而指向最初假定的角色。”[6] 就文学史而言,也存在着一个交互性逐渐活跃和不断被释放的过程。特别是现代主义出现以后的文学,更多的是一种读者的创造,作者在文本中留下了很多空白的、游移不定的点,阅读本身也就变成了一种游戏。
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认为有两种文本,一种是“可读的文本”(texte lisible),读者小心翼翼地服从作者的意愿,循规蹈矩,无所作为;另一种是“可写的文本”(texte scriptible),读者在这种文本中玩着无穷指涉的游戏,进行自由的创造,在两者之中,巴特心仪的是具有先锋性的可写的文本。[7]如果从一个更大的文化视野来看这些走向,就会发现可写的文本找到了全新的载体,并走向了极为广阔的大众文化空间,那就是网络、游戏和虚拟现实。在那里,大众进行着前所未有的自由创造的游戏。
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根据游戏改编的小说和电影不断涌现。数码电影《最终幻想》就是根据同名游戏改编而成。《银河飞将》被拍摄成电影,改编而成的系列小说已经出了6部。 除了职业性的创作以外,网络上出现了很多网友自己创作的以同名电子游戏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正在成为网络文学中的一大类别,具有网络小说“合作化”的特点。
电子游戏与传统艺术之间,除了相互改编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相互渗透关系。在艺术手法和风格技巧上它们也彼此借鉴。例如,在晚近的电影中,越来越出现游戏式的光影效果。在情节的进展上,一些小说和电影也借鉴游戏的练级、生命值、解谜、攻关等套路,迎合观众新的心理需求。这方面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科幻电影《安德的游戏》,节奏、视觉、调子、气氛都给人一种强烈的游戏感。
影视与文学一旦进入游戏,那就不止于简单的改编,而是开辟了全新的天地。在传统的艺术中,读者和观众可以观看不同的人生,但那多半只是一次性完成。在电子游戏中,玩家不仅仅是观看,还扮演、体验、创造不同的人生。玩家不仅是读者和观众,也是演员、导演、作者……简言之,就是世界的创造者。就媒介的融合而言,电子游戏为文学艺术增添了新的维度和自由度。
电子游戏的未来:上帝和作者已死,众生喧哗
在新一代艺术的融合中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一种指向:越界。这是一个越界的时代,人类主体正在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具有能动性,越来越不受拘限,而电子游戏就是这一趋向的最新载体。电子游戏结合了小说、绘画、音乐、电影等传统艺术的元素,融技术、欲望、幻想、现实、逃避性、参与性、交互性于一炉。从前在其它艺术中,由于媒介和技术的限制而受到阻遏的意志和欲望,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可以畅通无阻地宣泄出来了。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催生了众声喧哗和主体性空前活跃的新世纪,我们在赛博空间到处可见对无限的可能性的渴望、无止境的选择、跨历史的狂欢。这种渴望,一言以蔽之,就是读者、观众、玩家们要扮演上帝的角色。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说作者死了。但是读者还活着,而且他们要做上帝。这是一种古老的欲望,但是也只有今天才为这无数上帝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虚拟空间是一个没有法律,只有游戏规则的空间,玩家可以为所欲为,宣泄各种欲望,不用担心自己会被抓起来。即使失败了,也还可以去调一个个存盘文件,或者干脆就重新启动电脑。这是一场人类扮演上帝的游戏,而交互性就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成为上帝的努力:不受限制的视角、穿越时空的本领、创造毁灭的能力。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进步,电子游戏中的交互性会不断地发展。虚拟现实是人对超越现实的渴望,可以说,一切艺术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虚拟现实。今天,虚拟现实有了全新的载体:电子媒介,更清晰直观,更活色生香,更让人沉浸其中。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在迅速发展,计算机将能自动创造出具有众多可能性的交互式情节。当人们所有的幻想都能够“真实”地对象化、影像化的时候,其身份和自我认同必将发生巨大的改变。
另一方面,在虚拟变得越来越真实的同时,虚拟也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概念:虚拟经济、虚拟货币、虚拟社区、虚拟购物、虚拟教育……我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各种形态的虚拟。虚拟的现实与现实的虚拟,这两种朝向彼此的运动能够最终合流吗?这其实也是人类的一个古老的梦想的最新呈现:艺术的生活化与生活的艺术化。
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认为人的理性和感性存在着永恒的冲突,而游戏可以将这两者调和起来:“一言以蔽之,人只有在他是十足意义上的人时才进行游戏,只有在他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8]席勒所说的游戏是一种美学的理想,与我们今天的电子游戏看似非常遥远,骨子里还是有着相通的地方,它们都指向一种自由而又自律的状态。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席勒期许的游戏作为电子游戏未来发展的理想。
如果艺术也有制高点的话,文学和电影都代表过这个制高点。我认为,从现在到未来,更具有决定性的至高点是电子游戏。可以这么说:谁掌握了游戏,谁就掌握了人的想象;谁掌握了想象,谁就掌握了未来。
[1] 乔纳森·琼斯《对不起现代艺术博物馆,电子游戏不是艺术》,卫报,2012年10月30日
[3]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11页。
[4] A.L. 贝克《作为再现艺术的电子游戏》,Postgraduate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 9, No. 2 (June 2012)
[5] 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6] 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汪正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0页。
[8] 席勒:《席勒文集》第6卷,张佳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0页。
(作者严峰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扫码可见报告精华内容
澎湃城市报告,一份有用的政商决策参考。
由澎湃研究所团队主理,真问题,深研究。用“脚力”做调研,用“脑力”想问题,用“笔力”写报告。